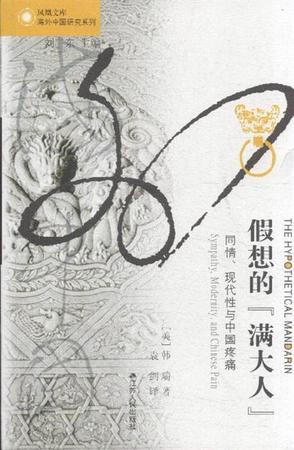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几年来学术界颇为热门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强汉盛唐”,还是“皇明大清”,都因为发生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而成为今人热衷的焦点。仿 佛历史上“盛世”于今真有某些相似之处。话说回来,今人之所以在意他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并非关注他人,只是因为距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难免 “心意彷徨”,想要从西方的看法中,找到自己几个世纪以来形象变迁,获得由衰而盛的依据。
不过,怀着此种想法,难免在过去“形象”的选择上,有了扬抑的侧重。故而推崇东方世界过去成就的《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等作品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可 这略嫌久远的往事毕竟难解“近渴”。何况在近代史上,中国形象还发生过多次变迁,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莫过于“满大人”的故事。
前不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钢铁侠3》中,与战无不胜的工业文明代言人小罗伯特·唐尼为敌的反派塑造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傀儡对手,为他起名曼达林(M anda-rin)———对这个名称,我们更熟悉的译法就是“满大人”。“满大人”虽不姓满,但本意里确实有点“大人”的意思,这是葡萄牙语对明代中国 “官员”的称呼,不过随着利玛窦的引介,该词传遍西方,遂成为“士大夫”的代名词。对此最著名的借用莫过于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 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的引用,他在该书中便用M andarins一词专指儒家学者,于是,德国学界也发明了G erm anM andarins一词,来指代曾经的容克贵族知识分子。
随着时间推移,“满大人”作为中国人这一“所指”的“能指”逐渐发生了意义上的变迁(或许伴随“傅满洲”等东方人形象的塑造),“满大人”离它原初的含义 越来越远。甚至成为了《钢铁侠3》中那个兼具傅满洲诡计,又徒有其表的傀儡。然而,“满大人”这一亦虚亦实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其实发生过颇为有趣的变 迁,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服膺于西方人的想象,正如《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研究教授韩瑞所 揭示的那样:“‘中国’(作为人种、作为民族、作为文化)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再生产了缠绕在中国与近代人类所发明的历史关联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它表 明满大人是中国人,因为他作为中国人就意味着他的中国人特征无关紧要。”不管怎样,这位“想象”出来的满大人实际上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表征的一部分,虽 然作者坦承“这本书的风格确属另类,读起来可能颇为费解”,但借助译者袁剑先生的努力,我们将有机会面对一个西方人眼中真正的“满大人”。
“满大人”的历史
作者从《中国服饰》和《中国的刑罚》两本19世纪之初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著作着手,揭开了弗兰克笔下,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拥有世界白银总量一半以 上”国度的另一面。与此巨大财富相比,《中国服饰》的作者,马嘎尔尼使团绘图员亚历山大在书中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所抱持的强烈好奇心”。在 书中,中国人的形象被一种民族志的描述呈现,并随着作者的独特视角使“中国乐手、乞丐或裁缝”这类不太常见的形象占到相当比例。紧随其后出版的《中国的刑 罚》则更通过一种猎奇的描述,将那种建立在独特风俗基础上的民族志观察,与更深层的法律、道德哲学层面结合起来。
尽管这些同样的观察在不久之前,诸如利玛窦的表述中,完全被当成中国财富与繁荣的一部分,但此时,随着欧美文化对“道德”与经济关系的重新建立(比如“新 教伦理”),转而成为财富积累方式不道德一面的渊薮。因此,这无可避免地成为“欧洲和美国人对那些无法表现出……对人类同情心”的文化,“加以干涉的文化 辩解的一部分,不管这种干涉是通过贸易、外交、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还是以战争的方式展开。”
“在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出版后仅仅过了40年,在贸易及外交方面的紧张局面……直接导致了中英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虽然作者暗示的这样一种联系的可 能性尚值得推敲,但“满大人”的形象也随着时间和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迁,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深罹鸦片之疾的满大人,变成了林呱画笔之下或者受巨大肿瘤困 扰,或者身染麻风病的形象。种种疾病虽然并不全由鸦片所致,但在患病中国人毫无知觉的表情下,渲染了某种对痛苦的麻木,以及绘画者(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 负罪感。“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患者的病症图片,而这身后则是西方对东方财富的暴力敛取, “通过将那种暴力看成是在西方的财政成就与某些中国人的死亡之间画上等号的一种重复”,满大人身体上的痛苦,成为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终极隐喻。
“到了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亚洲以及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之间的关联,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种老生常谈,开始出现了。”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实 践,导致中国人向世界不同地区的“离散”运动,将“满大人”引入了西方社会,“排华”与引进低廉华人劳动力之间的交替进行,推动了《黄祸》类型小说以及 “傅满洲”形象原型的出现。在各种小说中,中国人的形象几乎是预言性地与他们在20世纪末呈现在西方媒体中的印象不谋而合。“在小说所表达的接受中国人政 治统治的论调当中,所隐藏的是对资本主义未来以及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一种看法,即……劳动力及贸易的跨国网络的生产逐渐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孤立性与独立 性”,换句话说,满大人及其背后似乎是千人一面的中国劳动力,将把美国社会同化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而非产品的消费者,与之同时发生的,将是社会主体的消 失。正是基于这种恐惧,“满大人”拥有了“文明社会”永久威胁者的身份。
当然,随着二次世界大战拉紧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中国再次以浪漫主义东方的形象,成为抗拒现代性的梦想之地,正如罗素在1921年的信中所言,“在这个星 球上,我没有家园———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国家更加亲切,因为他们的人不残忍。”所有过去的满大人式的形象被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更新, “如果中国在1922年可以被当时世界上两大最具前瞻性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视作是一种‘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地缘性政治地位,它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关 系,与现代化的关系,其可能性就会‘在最为需要的时刻,为人类带来整个新希望’”。毫无疑问,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形象获得了其最早先形态的短暂 回归。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对垒,从赛珍珠那里获得的中国印象,逐步被压缩成一张平面的民族志图画。本书作者用一张针灸麻醉的照片, 表达了一种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复杂结合,虽然和一个多世纪前的肿瘤照片一样,“身体”依然成为满大人的隐喻,但这种螺旋上升的现代性进程,留给桑塔格或巴塔 耶的却是一种更复杂的,模棱两可的选择。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以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塑化尸体展览作为全书的总结。“从一种文化的视角来看,尤其是自从在中国获取大量尸体之后,这感觉就像是一种粗暴的 侵犯。”虽然外国观者延续了某个阶段的“满大人”想象,但这种主要用于医学教学和公众教育的展览,并未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不过作者依然指出,“即使将来 有一天,所有的塑化尸体都是那些欧洲志愿人士捐献出来的,那些想象的满大人全都来自拉丁美洲,那么所指涉的社会类型就将会在西方地理学与被称作‘中国’的 那种……他者的冲撞中保持其起源的某些化石遗迹”———其实,“满大人”只是西方文化想象的若干他者的集合,而已。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满大人”
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关于“中国”的文化研究作品,其缺点难免如偏好阶级分析的文化研究一样,好用似是而非的大量术语,模糊了本来可以清晰明了的结论;同时, 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屡见不鲜,似乎除了借用“身体”与“情感”外,很难在这个关于“中国形象”的话题中更上一层楼。
不过,从对全书的分析来看,在鴂舌的修辞之外,作者笔下的满大人渐渐与“中国”/中国人分离了开来。事实上,正如卢梭笔下屡屡出现的“野蛮人”一样,虽然 满大人最初无疑来自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想象与塑造,但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眼中某种“他者”形象的集合,满大人固然有着集体主义、千人一面,甚至 “缺乏痛感”的平面化形象,但其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其实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原始含义,成为一种更抽象的概念。与赛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不同的是,“满 大人”所指涉的文化内涵,已被其经历的话语结构变迁,摆脱了简单的政治地理学关系,成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一部分。
因此,当我们通过本书作者的笔触梳理了“满大人”的历史,了解了它与“中国”既近且远的关系,或许便不必再纠结于“中国形象”的话题。毕竟,这个想象的“满大人”已经更多属于过去。
日期:[2013年6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