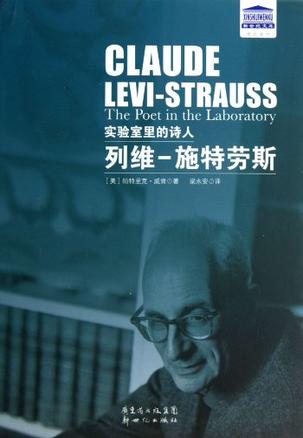
从他尚在人世起,列维-斯特劳斯便是一位不缺传记的学者。那些形式各异的传记中,早有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为向英语世界介绍“结构主义”而写作的《列 维-斯特劳斯》,又有法国评论杂志《新观察家》周刊著名记者迪迪埃·埃里蓬与其所作访谈式传记《今昔纵横谈》(一译《咫尺天涯》)。在其身前最全面的传记 是散文家、传记作家德尼·贝多莱所写的《列维-斯特劳斯传》,2009年去世之后,他的影响力不减反增,学者兼作家的帕特里克·威肯为他出版了迄今分量最 重的传记《列维-斯特劳斯:实验室里的诗人》。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便“自外于学术争论”的列维-斯特劳斯,曾在1979年对《新观察家》杂志发表了如下发言,“这不是我认识、喜欢或是还能想象的世 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世界。”打那之后,他便隐居于勃艮第的利涅罗勒镇的法式度假别墅,“坐在宽敞的起居室,利用从大窗户和落地窗照进来的自 然光写作、处理盈案的来信,或是翻阅19世纪初编成的那套全72册的自然科学百科全书”———这一副旧式法国绅士作派———只是偶尔尽一下卓越知识分子的 职责,出席访问,参加会议,“当其他人发表意见或自我辩护或大声驳斥对方时,列维-斯特劳斯只是静静坐着,什么都没有说。”人们很难将此时他与《忧郁的热 带》中那个穿越巴西丛林,充满动力的人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当罗兰·巴特与萨特(1980)、拉康(1981)、雅各布逊(1982)、雷蒙·阿隆(1983)、福柯(1984)、布罗代尔(1985)、杜 梅泽尔和波伏娃(1986)相继去世之后,在他一枝独秀的最后20多年生命中,原本需要与他人分享的光荣,或许都只照耀到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几乎处于隐居 状态的人类学家一人身上了。对于传记作者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唯一的传主减少了传记作家们的工作量,但也让作者把原来的激情全释放到同一个对象身 上。有涯之生,如何演绎出无穷故事,倒是对传记作者最大的考验,不过好在,各位作者搜求文献,各辟蹊径,对读者却是最大的福祉,借助每一本不同传记的侧 重,终为我们塑造那位完整的列维-斯特劳斯。
本书作者威肯曾就读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及拉丁美洲学院,曾在巴黎与里约热内卢长住,既有人类学背景,又是研究巴西历史的专家。正是这段学术与生活经历,让他有机会发掘出前人未曾引用的材料。
在热带中萌芽
在和之前传记一样提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犹太背景和早年学术经历后,作者并不满足于用后来的《忧郁的热带》点缀列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巴西之行。借助一本 2001年出版的巴西人类学家法利亚的《另一观点:北山考察日记》,本书完全从观察者的视角充实了1938年的那次亚马孙之旅。
那一年,列维-斯特劳斯组织了一次沿着龙东电报线的田野旅行——— 这是一条由军官兼“印第安人保护局”创立人“龙东”计划并实施铺设的现代通讯线路,冥冥之中为列维的学术生涯铺好了轨道。1907年,这位“对印第安人困 境深感同情”的现代主义者“奉命把巴西的电报网络从库亚巴延伸至亚马孙河”沟通玻利维亚,让人莞尔的是,龙东电报线铺好后“从不曾正常运作过,……在10 年施工并造成数百名工人死亡之后,电报线的功能已悄无声息地被无线电发报机所取代。”于是,列维一行便沿着“绵延到天边”的歪扭电线杆,寻找他的波洛洛 人。
“十五年后写作《忧郁的热带》时”,威肯写道,列维-斯特拉斯会“忆述他与为数不多的印第安人的相处经历(其中充满沟通上的挫败)”,对其而言,“这些在 高地上孤独流浪和邋里邋遢的土著就是卢梭笔下的‘自然人’。”这次为期8个月的考察,构成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田野经历,著名的《忧郁的热带》中最引人入胜 的部分,不过,透过法利亚的眼睛,我们也看到,“废弃的电报站……被传教士用作基地,准备让当地原住民改变信仰”;他们遭遇的一个吐比卡瓦希普人的村落 “几乎无法在森林里存活”,“有些妇女的项链上串着空弹壳,透露出他们从前可能跟白人发生过冲突。”
列维-斯特劳斯的确是一个实践的卢梭,但他看到的不是纯粹的“野蛮人”,他看到的是与现代文明交锋过程中并不占优势的原住民。
30年代末的旅行和40年代初的体验,奠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路径:同情原住民,对发展主义保持谨慎的疏离(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对“浪漫原始主义”的推崇,也不是投身反理性、反现代之流),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更彻底的科学而理性的“结构主义”。
实验室里的“结构主义”
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是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认为异文化成员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抨击(“一个对萨特炮火全开的攻击”,威肯语),虽然在今天看 来,这只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温和版本———我们已经逐渐接受文化的多元形式,不再以唯一的标准苛求他人———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刚经历奠边府蒙羞,以及 制肘于北非的法国,这更多的是带有人道主义的味道。我们看到,列维不仅强调“野性的思维”之存在意义,而且试图在他新近拥有的人类学实验室里找出“神话思 维”的基本结构。而这一思路其实肇始于更早的阶段。
他在40年代末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在书中讨论、涉及全球数百种人类群体“亲属关系”,并试图从中归纳一些“基本结构”的 根本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亲属制度”本身,而是为了提出一些全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结构”。这本著作囊括世界所有主要人群的做法,将澳洲阿纳姆地、印 度阿萨姆、斐济、秘鲁的社会与法国等欧洲社会相提并论,并不是为了如马克思等古典作者一般划分社会的高低等级,其实是将各个社会表面不同的复杂程度全部略 过,从最基本的“亲属关系”中讨论他们的普世本质。
他对亲属结构的分析也许值得商榷,但由此延伸出的“结构主义”,却因其对人文世界的科学尝试成为二十世纪后半期前段,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关键词。许多人会 从索绪尔和雅各布逊那里寻找“结构主义”的根源,本书作者也概莫能外,但是,威肯遗憾地只用一句,“列维-斯特劳斯建议巴特一读普罗普写的《民间故事的形 态学》”,就绕过了这对结构主义影响极大的“第三个人”。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中专用一章来研读俄国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有关民俗研究的“结构与形式”。普罗普认为民间/神话故事版本的不 同,是因其各种要素,按不同形式组织而成的———只要改变组织方式,将故事内容重新排列,就能得到一个神话的新的版本。列维-斯特劳斯在此基础上认为,一 个神话与一个人群的对应是固定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构成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构成方式与该社会结构也是一致的。简言之,普罗普的“神话” 是可变的,而列维的“神话”是有固定结构,不变的;这种结构,反映了结构拥有者的世界观。
并不悲观的保守主义者
虽然对“结构主义”的把握欠缺,作者最后提到,列维-斯特劳斯是个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他是对的。一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质疑“反种族主义”的立 场,列维-斯特劳斯虽然“激烈地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这种努力,是在助长“迈向一个世界性文明,其总倾向是摧毁古代的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带来了我 们的美学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
威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因为够长寿,以致看得见自己最担心的噩梦成为事实:世界人口无情的膨胀、环境遭到肆意破坏、许多发展了几千年的文化被消灭”, 这与他“半个世纪前即已弥漫在《忧郁的热带》里的悲观情绪”一脉相承。对于一个看过了整个20世纪的人来说,不能要求更多,作为诗人,列维-斯特劳斯并不 盲目推崇遗世独立的“野蛮人”形象;作为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努力揭示“简单社会”的普同结构,使之不致沦为“复杂社会”博物馆中的人类标本。从这一点来 看,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悲观,他的“神话学”事业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尽管追随者日罕,但这种对普世性的追求,已经借助这位“诗人”之笔成为人类思想财 富的一部分。
日期:[2013年3月3日] 版次:[RB03] 版名:[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